聲無哀樂 - 絕色的推拿
- 聲無哀樂
- 2025年7月21日
- 讀畢需時 3 分鐘

絕色通常都解作絕對的美色。黃耀明〈絕色〉除了這一解之外,林夕玩另一解,絕指斷絕,色取佛家義,指花花綠綠的紅塵。歌曲主角是盲人,未知是先天或後天盲,但視覺上無疑是斷絕紅塵,卻同時談著戀愛。情人眼裡出西施,盲人眼裡出的是什麼?婁燁《推拿》的一場戲展現了盲人眼裡出的也是西施。

先天盲的推拿店沙老闆招待客人時,聽到他們說店裡的一個女師傅都紅很美,身材很好。說了幾次後,老闆想追求她,摸她臉,說:「美到底是什麼,得憂鬱症了,天天想,沒日沒夜地想,就是想看一眼。都紅,都紅,美很吸引人是吧?」都紅後來拒絕他:「你以為你是愛我,其實就是你的虛榮心,迷戀上了一個概念,僅此而已。那不叫愛情,你還曉得啊?沒有那個女人是看不到愛情的,眼瞎的女人尤其看得到。」

老闆靠撫摸而大概猜到都紅的長相。那種猜,我不敢說是什麼,始終盲人的世界我不認為我能理解。可是,迷戀概念卻是健全人都不能避過的劫。穿著中學校服的日子,迷戀其他學校的女生,可能只是因為我們這群臭男生覺得她美。連有眼的人都會迷戀概念,盲人在聽到健全人說的美,就更加相信都紅真是美。一相信都紅美,西施就出現了。

只是都紅心裡有另一盲人,對方心裡又有一個健全的妓女。在這條愛情鏈中,只有最後一對在一起。妓女稍稍流露出對盲眼男生的關心和好感就被同事恥笑,男生後來不想她接其他的客而被打。種種事情妓女都看在眼裡,同時像都紅所說,眼瞎的女人尤其看得到,妓女的肉眼仍在,但發現在愛情面前肉眼是瞎的。二人遠走高飛,男生開了一間小推拿店,上樓回家時,他聽到女生在走廊洗頭抹頭,站住笑了。他一笑,我只想起〈絕色〉的一句,「但信花灑聲裡聽到你表情」。聽得出表情應該不是健全人做到的事,健全人都太依賴肉眼去看別人行為和表情,卻輕視了展現真實反應和情感的細微之處有時是肉眼看不到的。我跟盲人的差異竟然是那麼小,他們說「我也天生不會用眼睛愛人」,我會說我老天爺給我眼睛,但是我從來不懂得用,一直以為有眼,原來只是無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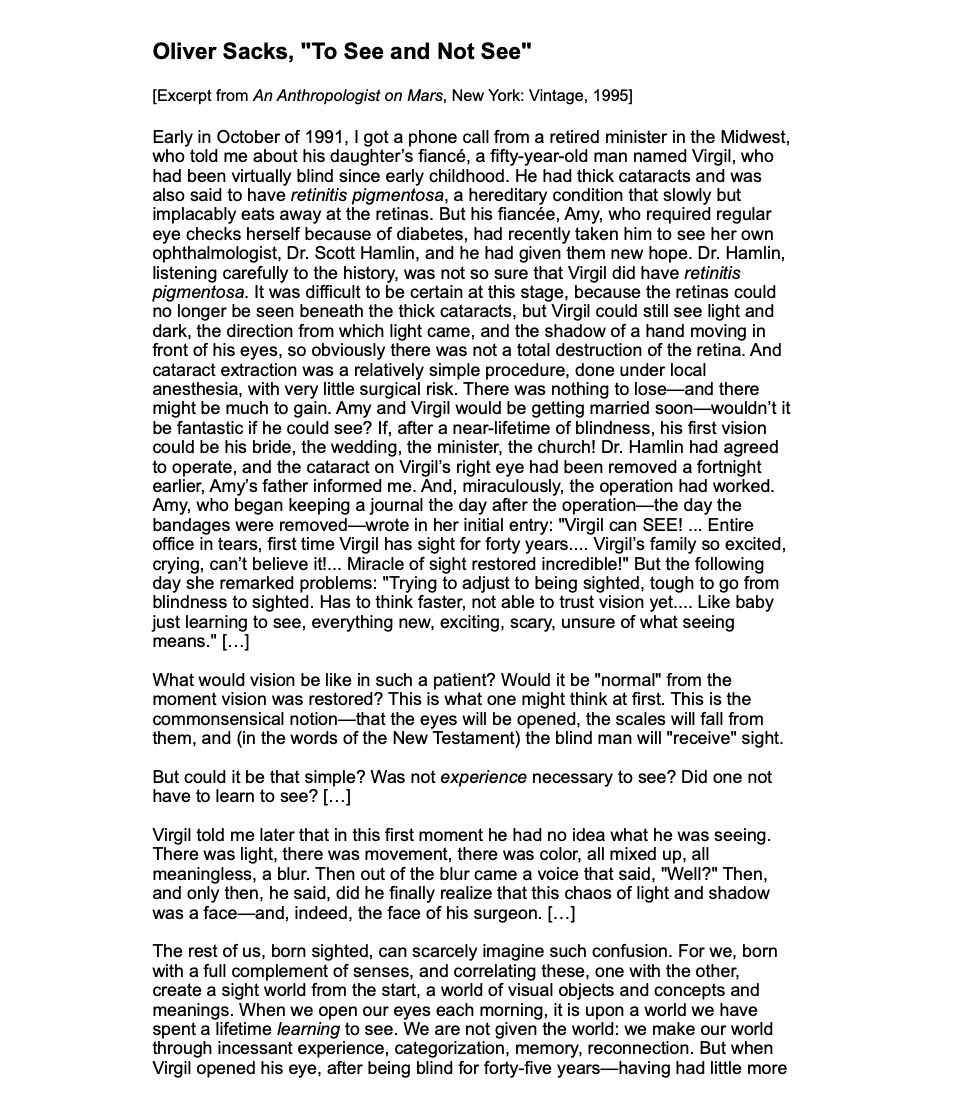
不過,如果被問到你要不要眼睛?我和盲人的答案卻會不同。我一定說要。英國醫生奧利佛.薩克斯(Oliver Sacks)的文章〈To See or Not to See〉卻指出視覺並不是開一扇窗,而是一種使用腦袋學習的能力。如果盲人已經是長期盲,腦袋會認為不需要學習視覺,後來即使重獲視力,腦袋也學不懂了,所以對盲人來說視覺是負擔,強迫他們用視覺去處理世界會大大影響他們情緒。薩克斯的病人最後被容許用回他五十年的盲人舊方法跟世界打交道。讀了這篇文,我才明白收結那句「免得你有日懷著絕色一刀/插心內」指的是重獲視力去看本來看不到絕色,隨時引發憂鬱症。眼盲的沙老闆憂鬱於「美」,但難保他開眼看到都紅的「美」原來不美,更令他憂鬱。都紅的絕色變成了一把刀插入沙老闆心中,但他應該更想毀掉這視力。即使毀掉,已經看過都紅的樣貌卻是不能倒帶。這段回憶會一直在他腦中永恆重播,像林夕〈永恆〉的一句,「讓容貌刻在途上終生欣賞/直到化做石像」。只是未必是欣賞,若是憎恨,那就更可悲。
台北車站地底有間真好盲友按摩站,我最初不熟悉那裡交叉錯蹤的地下街,常常行錯路,好幾次走到按摩站才走回頭。心思在找路,所以沒有留意他們。後來熟悉了,就很少走到那邊。若然剛好經過,我不敢詳看他們,怕不禮貌,但只要稍稍望一望,就看到他們的表情不像健全人朝九晚七的沮喪,稍稍聽一聽,就聽到他們細聲講大聲笑。只是我仍未學懂從按摩中聽出他們的表情。
《絕色》
主唱:黃耀明
作詞:林夕
作曲:梁基爵
IG:@cheukyiuuuu
一個欣賞阿多諾對音樂的態度,但不完全認同他音樂哲學的人
圖片來源:婁燁《推拿》,http://timothyquigley.net/



留言